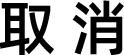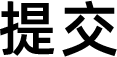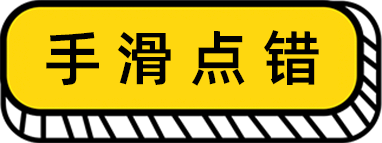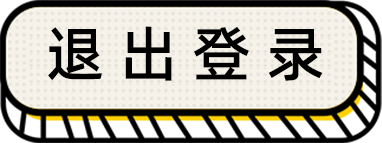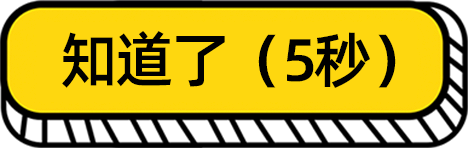弘治四年(1491年)十月,丘濬以太子太保、礼部尚书兼“文渊阁大学士”,参与国家大政,遂行宰相之职。然而就在他入阁前几个月,原担任内阁首辅的刘吉却被免了职,这一进一出,刘吉大生疑惑,认为是丘濬背后搞的鬼。刘吉为此大为恼怒,私下里骂他为“南蛮子”,还特地撰了一副对联侮辱他:“貌如卢杞心尤险;学比荆公性更偏。”意谓丘濬像貌不雅,丑如唐代的奸相卢杞,而才学与宋代的王安石一样,性情比王安石还要偏执。这显然是不顾事实的恶意中伤。
刘吉之所以被踢出内阁,是因为他耍手段阻挠孝宗皇帝的“家事”,与丘濬全无干系。而刘吉此人的“为官之道”早为当时朝野人士所不齿,原来,他做官专为混日子,四面讨好。在明宪宗(孝宗之父)时,他与万安、刘珝同为内阁成员,安为首辅。三人专务吃喝享乐,尸位素餐,国家大事由太监汪直专政把持,内阁成为虚设,故人称此三人为“纸糊三阁老”,孝宗早就无意留他。然而尽管这“纸糊三阁老”的所作所为常引起公愤,遭到言官的弹劾,但这个刘吉惯来圆滑善变,你越弹,他越升官晋爵,孝宗即位后,尽管并不看好他,还是能够留任,真是像棉花一样,越弹越发。所以在这之前,早就有人送他一个绰号叫“刘棉花”。后来,刘吉打听得起这绰号的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国子监老生员。而凑巧的是,当时丘濬官居礼部侍郎掌管国子监(即国家太学校长),因此刘吉便怀疑讥讽他为“刘棉花”一事定出于丘濬的主谋。
但丘濬为官清廉正直,若想找他的茬子,实在是无懈可击,于是“啃不动硬的,专挑软的捏”,以他内阁大学士的权势,奏请宪宗皇帝下诏,今后凡是三次考试不第的举人一概不许再试。不仅如此,还借机大整那些与己不合的朝中大臣。这些行为,都是丘濬亲眼所见,当然与他水火难容。刘吉既以对联侮辱丘濬,可是他还未离开京城,也有人给他送了一副对联,道是:“泥塑纸糊,全没心肝如木偶;弓弹椎碾,更无骨节似棉花。”因为当时,除了“纸糊三阁老”外,社会上还有“泥塑六尚书”之讥,所以谓之“泥塑纸糊”。刘吉看到这副与他针锋相对、入木三分的讥刺对联,可说是气急败坏,又怀疑是丘濬这个“南蛮子”所为,但罢官在即,大势已去,也只有干瞪眼而已。
据《明史》所载,弘治四年,与丘濬同时入阁的还有洛阳人刘健。刘健其人,与丘濬一样,博学多识,闭户苦读,处事稳健,人称“木强”(意即刚强不屈)。他与丘濬一样都是因为参与编修《宪宗实录》有功,被提拔为礼部尚书,又是因此而先后进入内阁。但此前,丘濬还参与编修《英宗实录》,那时他还只是个“侍讲学士”,却在编修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刚正不阿的耿介气质。
当时参与编修的某些人为讨好宪宗,主张把被明英宗(宪宗的父亲)处决的民族英雄于谦作为“叛逆奸臣”写进实录中。丘濬力排众议,坚决抵制于谦是“叛臣”的诬陷之辞,公开置辩:在“土木堡事变”后,若没有于谦的誓死拱卫北京,大明的江山早就岌岌可危了!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,是非曲直大家心里都明白,为何还要让于谦来背这“叛逆”的黑锅?由于他义正词严的置辩,最后没有将这种诬陷之词写入《英宗实录》。这一史实,说的是明英宗于正统十四年(1449年)听信宦官王振的怂恿,轻率出兵,被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虏,其后,北京被围,明朝面临亡国之险。兵部尚书于谦受命拱卫京都并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珏为景泰帝,击退了瓦剌部的围攻。
不久,明英宗被也先释放回京,却在亲信徐有贞等的策动下,发起“夺门之变”,废了景泰帝,重登帝位,改元天顺元年,并在徐有贞等人的唆弄下,诛杀了护国有功的于谦。刘健是英宗改元后,于天顺四年中进士的,对这段史实应十分清楚,对丘濬为于谦辨白的事也应是明白的,是否同意丘的观点另当别论,但对丘濬的为人从此应有所了解。
丘濬生性耿直,遇事认理不认人。他对刘健的好学深思颇有好感,所以两人在内阁相处,还没有听说过像与刘吉那样的针锋相对的矛盾。但《明史·丘濬传》说他们两人有时因某些时政问题在朝堂上强辩不休,各不相让。有时争到激烈之处,丘濬甚至将官帽子掷于地上,表示即使不做官也要坚持真理。但争论归争论,私下里两人也没有像与刘吉那样誓不两立。
有一次刘健对人说:“丘仲深(丘濬的字)有一屋子散钱,但没有串钱的绳子。”意思是说丘濬虽然学问广博,但缺乏系统,散乱无章,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不多。丘濬听到后,也不谦让,立即反讽道:“刘希贤(刘健的字)有一屋子串钱的绳子,但没有散钱。”意思是刘健处事虽善于抓住要害,善断多谋,但见识不广,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。两人可谓各有所长,都见到了对方的长处和短处。
丘濬与刘健在内阁相处的时间不长,弘治八年(1495年)丘濬逝世,此后,刘健还在内阁任职,一直是孝宗皇帝所倚重的能臣。
在弘治内阁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王恕,年纪比丘濬大。孝宗即位时,王恕本已退休致仕,但念及他在宪宗朝执掌吏部的功绩,特亲自下诏请他还朝。作为“三朝元老”,王恕确是有功之臣。他执掌吏部期间,为朝廷选拔了许多能臣,门生故旧遍布朝野,“人脉”极厚。但晚年还朝之后,却有点“功德圆满,傲然自恃”的情怀。每天上朝时,都是他在皇帝面前首先奏报,别人都等候他讲完才开腔。他对丘濬的入阁似乎很不满。虽然他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,一贯也讲原则,不许人行贿买官,但看到丘濬却从不因为他身居吏部而对他有丝毫亲近附和的表示,反而在朝政问题上有时不惮与他争辩是非曲直,让他感到被轻忽挑战的味道。故此两人从不来往,见面也不打招呼。
弘治六年,王恕主持吏部考核天下群吏,决定罢黜二千多人。丘濬上奏反对,认为这其中有的官员上任还不满三年,如果没有贪污渎职等行为的话,不应统统罢黜。结果皇上准奏,经过认真考察,留下九十多人。王恕因此觉得很没面子,益发恼怒丘濬。但丘濬入阁不是走王恕的门路,而是孝宗皇帝亲自下诏选定的,所以对于王恕的迁怒不以为意。而王恕的门徒们却造谣说这九十人中有丘濬修《宪宗实录》的同僚,希望通过丘的关系得到提拔重用,却被王恕刷掉了,所以丘才发难;又造谣说,丘之所以能入阁是因为向皇上进奉一种“阁老饼”,皇上吃了喜欢,才提拔他。
丘濬对这些流言一概不予置辩。又有一太医院判名刘文泰,曾经请托王恕关照自己的升迁问题,但达不到目的,心存怨愤。刘经常到丘濬家看病,关系甚密,从丘濬处了解到王恕退休在老家时,曾让人刊印了一本《大司马三原王公传》,广为流传。刘文泰弄到该书读后认为该传中,王恕自比为周公,“彰一己之善,显先帝之过”,失人臣之礼,于是写成奏章,请被王恕除名的御史吴祯帮忙润色,连同本书一起告到皇帝那里。王恕急忙为自己辩解,并声称刘文泰的奏稿出自丘濬之手,希望一并追究丘濬之责。孝宗下诏将刘文泰逮捕入锦衣卫狱审问,才知道实出自吴祯之手,与丘濬无关。
孝宗因上述种种问题,于是对王恕有了看法。而王恕本想借此机会扳倒丘濬的企图也落了空,故而恼怒在心提出要退休致仕。孝宗马上就批准了,并且不按惯例给予他应有的待遇,算是灰溜溜滚回老家去了。但王恕门徒众多,而明代的官场风气“不务举贤进能,又不平心静气,而专务于分门立户,各怀偏见”(《明史·邹元标传》),所以丘濬在这件事上一直处于被指责的尴尬地位,连清代的纪昀在评价他的《大学衍义补》一书时竟也说他“相业不可称”,“其人不足重”,显然是不顾史实的过分贬抑之词。